谈到中国美术史,八大山人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。尽管他去世只有三百多年,但其身世却已迷雾重重,特别是关于他的由僧入道之说,更是扑朔迷离。在论及八大山人时,人们多认为他先僧后道:早年为躲避清廷追杀,遁入空门,后又还俗,信奉道教,变为羽客。南昌著名道观青云谱即以其为开山之祖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?如果说八大山人曾经为道,那么他是在哪年入道,道号是什么?在他生前身后很长一段时间内,人们在对其诸多的记载中为什么没有找到他做道士的点滴文字?在他书画作品的大量题跋中,又为什么没有任何道家思想的流露呢?答案只有一个——八大山人从未做过道士,更不是青云谱的开山祖。尽管八大山人涉道之说为谬论已有铁证,但因各种原因,在学术上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,而且还在不断被沿袭。在一些美术史专著、学术论文和美术作品中,晚年的八大山人都是以道家的面目出现,继续影响着美术史界和宗教界,从而导致了人们对八大山人作品的曲解和误读,对其后期大量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佛学、禅宗,尤其是曹洞宗的倾向无法解释,对他在离开佛门之后的晚年还为明代丁云鹏《十六罗汉图》作《十六应真颂》(其中大量引录佛经和禅门话头)感到不可思议。

《山水花鸟》册页之一
八大山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(一说第十七子)朱权的九世孙,名朱耷。明亡之后的一段时间内,清政府对明朝皇室成员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。遭遇家国之变的朱耷为保全性命,于顺治二年(1645)隐居江西奉新山中,顺治五年在进贤县介冈灯社剃度出家,顺治十年投弘敏禅师座下。禅师俗姓陈,字颖学,法名弘敏,号耕庵老人。他为朱耷取法名传綮,字刃庵,号雪个。自此,师徒二人或同处一寺、或外出游历吟唱。八大山人追随师父二十余年,成为弘敏禅师得意法嗣,被称许为“禅林拔萃之器”。顺治十三年,八大山人随弘敏禅师到奉新新田乡芦田创建耕香院。禅师圆寂后,八大山人承其衣钵,主持耕香院,为禅宗曹洞宗第38代传人。他潜心研究佛学与艺事,从学者数百人,俨然一代高僧。

《山水花鸟》册页之二
康熙十六年(1677)末,应县令胡亦堂之邀,八大山人离开禅院,南下临川。据清代邵长衡所著《八大山人传》记载:“临川令胡君亦堂闻其名,延之官舍。年余,竟忽忽不自得,遂发狂疾,忽大笑,忽痛哭竟日。一夕,裂其浮屠服,焚之,走还会城。独自徜徉市肆间,常戴布帽,曳长领袍,履穿踵决,拂袖翩跹行。市中儿随观哗笑,人莫识也。”康熙十八年,八大山人去临川一年半后,回到南昌,从此还俗。这时,其绘画艺术已趋于成熟。邵长衡描述道:“山人工书法。行楷学大令、鲁公,能自成家;狂草颇怪伟。亦喜画水墨芭蕉、怪石、花竹及芦雁、汀凫,翛然无画家町畦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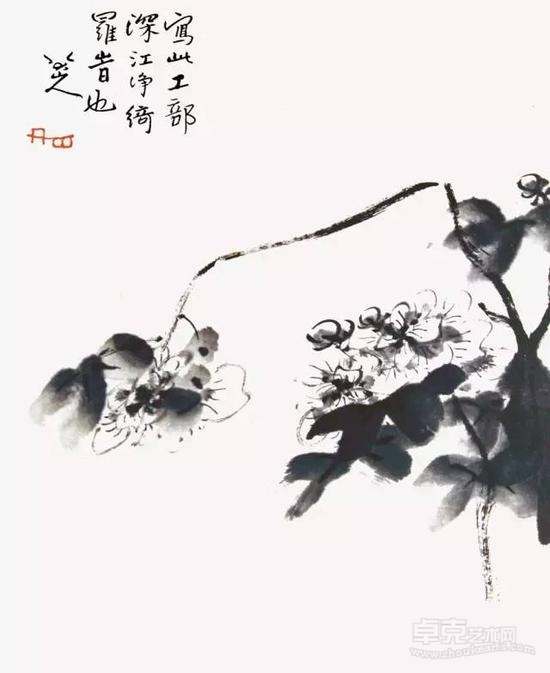
《山水花鸟》册页之三
八大山人主持耕香院之时,南昌附近有一道观青云谱,奉东晋道士许逊为祖 师。其宣扬“由真忠至孝,复归本净元明之境”的道教新派别──净明道,又称“净明忠孝道”。时值传到朱道朗(1622—1688)一代。朱道朗原名朱朗,号良月,道号破云樵者,因皈依道教,更名朱道朗。顺治十八年(1661),朱道朗在距南昌东南15里的定山桥附近修建宫观,历时六载,于康熙六年(1667)建成,取名青云谱。14年后,朱道朗主持编修了一部《青云谱志略》刊行于世。该书详细记载了青云谱的历史、规模、建制,“净明派”的教义、教法,以及参与创建青云谱的人物、吟咏青云谱的诗文等。八大山人所在的耕香院与青云谱相去不远,虽是僧道两家,但彼此也有往来。《青云谱志略》的作者中不乏八大山人的朋友,他们与八大山人常有酬唱之作。如作者之一的杨大鲲,曾与八大山人同游南昌西山,留下了《洪井洞诗》:“山光际晚空烟靓,雪公携我寻洪井……山僧指我旧飞梁,春荫碧蘅无人领。”(清魏元旷编撰《西山志略》)再如另一作者周体观所作《雪公画梅于吴云子扇头旷如也殊有幽人之致,为题短句》:“一树梅花断续出,惊之细蕊照寒芜。就中如许闲田地,或恐元来是两株。”两人所说的“雪公”即后来的八大山人,他当时的释号为“雪个”。其他作者在《青云谱志略》中的文章里多次提到过“朱良月”“良月师”,却从未提到“八大山人”或八大山人早期的一些名号。可见,在青云谱建成后的一段时间内,八大山人与朱良月僧是僧、道是道,二人身份历历分明,没有丝毫混淆的地方。

《山水花鸟》册页之四
青云谱道观自朱道朗后,代有兴衰,在风云变幻中薪火相传,延续了二百多年。至20世纪初,因清政府对道教的限制,加之西方宗教的传入,青云谱还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。“道院百间随风寥落,一片荒烟,不第草木含悲,即文士亦裹足矣”(民国九年版《江西青云谱志》),已是岌岌可危。此时中国正处在动荡不安的年代,清王朝日薄西山,风雨飘摇,各地义旗高举,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”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。而八大山人的艺术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历史的沉淀,越来越显现出巨大的魅力,并深刻地影响了有清一代的书坛画界。他作为明朝遗民,不肯与清政府合作,从不用清朝年号,以书画表达对旧王朝的眷恋,用象征手法抒写心意。其作品造型极为夸张,鱼、鸟之眼一圈一点,眼珠顶着眼圈,一副“白眼向天”的神情。作品表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——孤傲不群、愤世嫉俗,充满倔强之气。此时的八大山人已经完全跨越了艺术的范畴,在艺术和政治上具有了双重象征意义,成为反清复明的一面旗帜,受到追捧和敬仰,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所看重。一些人甚至用八大山人“明遗民”的名望大肆宣传。

墨荷图
光绪二十六年(1900),徐忠庆(1868—1928)主持青云谱,成为该道观的第十九代掌门。徐忠庆年富力强,上任后为振兴道观,延续香火,可谓殚精竭虑,不遗余力。尽管如此,虽有所建树,但起色不大。他深知,如不想办法提高知名度,青云谱就难以恢复昔日的昌盛。徐忠庆想到了名声如日中天的八大山人,于是采用偷梁换柱、移花接木之法,把青云谱的开山之祖换成了八大山人。他从1913年起便开始组织人写文章,为将来修《江西青云谱志》做准备。在他的授意下,原来康熙年间《青云谱志略》中江西按察司副使周体观所著《定山桥梅仙道院记》(青云谱在梅仙祠废墟上重建)一文,被改成《青云谱道院落成记》。其中编造了一段“逮有明之末,宁藩宗室裔,自称八大山人者,伤世变国亡,托迹佛子,放浪形骸之外,佯狂于笔墨之间,后委黄冠,自号良月道人,又字破云樵者”(民国九年版《江西青云谱志》中《青云谱道院落成记》一文)的内容,把朱道朗和八大山人混为一人。康熙年间修的《青云谱志略》中的《定山桥梅仙道院记》里根本没有这段话。光绪年间编辑出版的《南昌文征》收录了周体观的这篇文章,同样也没有这些内容。此亦可为佐证。前面说过,周体观为八大山人题画时称他为“雪公”。在他们交往期间,八大山人在奉新耕香院做住持。这一时期八大山人使用并在书画中签署的名、号,也仅为“释传綮”“雪个”“刃庵”和“个山”等。“八大山人”这个名号是在周体观死后多年才用,周体观生前不可能预料到。

芦雁
与八大山人同时代的陈鼎和邵长衡分别著有《八大山人传》,还有当时龙科宝的传世美文《八大山人画记》。其中都有对八大山人曾出家为僧的叙述,但都只字没提他还做过道士。清康熙四十一年(1702),八大山人77岁的时候,他的一位叫吴埴的老友题他的画册,也只说其当过和尚,并没有提及他做过道士(此论述可见谢稚柳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《中国画家丛书·朱耷》)。八大山人从约1681年还俗之后到去世,有二十多年的时光。这段时间并不短,但除了徐忠庆编造的《江西青云谱志》外,没有任何典籍记载过八大山人曾经入道。再者,在八大山人的诗词和书画题跋中,包括那幅记录八大山人身世信息密码的《个山小像》中,佛家的典故、禅机和隐语比比皆是。他的释号繁多,如“传綮”“刃庵”“个山”“个山驴”“人屋”“驴屋”等及后来的“八大山人”,在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上频频出现,唯独未见他在书画上题过道号或留下道家的任何片言只语。自1684年始,其作品出现“八大山人”四字署款后,其他名号皆弃之不用。陈鼎的《八大山人传》中说八大山人解释自己的这个名号时,言曰:“八大者,四方四隅,皆我为大,而无大于我也。”“八大”出自佛家的《八大人觉经》。这是佛家的一篇重要经文,说明诸佛菩萨等大人应觉知思念之八种法,以作自觉、觉他之修行。清张庚在《国朝画征录》中称:“甲申后,号八大山人。或曰:‘山人固高僧。尝持《八大人觉经》,因以为号。’”郑板桥在《题屈翁山诗札,石涛、石谿、八大山人山水》的诗中写道:“国破家亡鬓总皤,一囊诗画作头陀。横涂竖抹千千幅,墨点无多泪点多。”张庚和郑板桥都肯定了八大山人的僧人身份,而他们都与八大山人相隔不过几十年,此时八大山人是僧是道应已盖棺论定。还有一说,佛家理想的天国是以须弥山为中心,四周有八大山环绕。“八大山”中“人”,就是环绕在佛左右的人,是一位对佛有信心的崇仰者,一位在家的佛弟子。我们虽然不知道八大山人离开佛门的真正原因,但通过八大山人一直使用这个释号,就可以断定他至死佛心未泯,哪里又会去做道士呢?

松鹿图
综上所述,八大山人没有做过道士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我们深信,随着对八大山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有关资料的进一步发现,这团历史的迷雾终将会被彻底拨开。






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0602号
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0602号